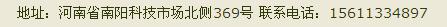分享会拍一部纪录片有多少坑澎湃在线
原创PlanJPlanJ
年8月1日,纪录片导演范俭和杨深来在线上分享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武汉拍摄的作品。
范俭的作品《被遗忘的春天》记录了一个大型社区在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冲突,疾病带来的猜疑气氛令人印象深刻。随着时日推移和疫情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这种无处不在的猜疑已经变得愈发具有象征意味。
杨深来的作品《蓝盒子》医院ICU在疫情后期的景象。医院是武汉承担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的主要医疗机构之一。
在分享会上,两位导演坦诚地谈到了他们遇到的困难甚至挫败,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以下为分享会实录的上半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夏佑至:《被遗忘的春天》我看过不止一遍,看到时候有一种不断增强的感觉,就是范俭拍摄的这个社区从一个很具体的地方,慢慢变成了象征空间。特别是反复看到当你们拍摄的时候,这个社区的居民也在拍摄你们,用他们的手机,或者站在旁边用非常复杂的眼神看着你们。我从里面感到一种疑惧的感觉,怀疑、恐惧,甚至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怨恨。通常,有人生病了,特别是传染病,有时候会怨恨别人。但在电影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没有生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怨恨那些生病的人。
片子里的那位基层干部,她非常辛苦,做了很多琐碎具体的工作,所有一线的事情她都在介入其中。但反过来,她并不能因为她做的事情得到其他人的认可。人们对她的态度,也是有质疑,有怨恨。可能范俭拍摄的这个时间点上,武汉人都是处在一种精神紧绷的状态里面,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我们来看整个的新冠疫情,从武汉发展成全国性的疫情,然后从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发展成世界性疫情,甚至引发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怀疑和恐惧。
所以今天来看这部片子,和片子刚上线的时候看的感觉不一样。这是咱们做纪录片这一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我先介绍一下范俭。你当年在武汉大学学的也是新闻吗?
范俭: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这次要感谢澎湃新闻,愿意和我合作(《被遗忘的春天》)。原本我即便是想拍,在这样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情形之下,也去不到那里;就算你去到那里,在当时的武汉,很多地方你都进不去,如果你没有一个证件或者说媒体资质的话,在武汉你要想进入一些现场进行拍摄,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这样一个前提。
确实,就像夏老师说的,在这样的一个社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们看彼此的眼神,跟往常都会有差异。
我们几乎每天都去这个小区,我们的行踪、我们去了谁家、见了什么人,很快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们在工作的某个地点会被拍照片,我们的影像早就被散布在小区的业主群里边,很快。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其实我真正见的人、聊天的人没几个,我们在小区里行走,有的时候也看不见谁在拍我们,但是也许就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出现在了业主群的讨论里面。
有趣的现象之二,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出现微妙的、戏剧性的,甚至是略微夸张的变化。比方说我们去了多次蔡大姐家,她老公得了新冠,然后她就表现得很焦虑。我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我还是挺喜欢这家人的,我想帮一下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出来买东西很不方便。她也不敢出来买,怕别人议论她。我有一次就买了一些肉给她送过去,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好久没吃肉了。结果第二天我去到另外一个阿姨家里,那个阿姨就有点质问我的感觉,说:“你们为什么专门慰问她家不慰问别人?”这听上去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吧?我也不是要去慰问吧?我怎么就成了一个慰问别人的人。而且,就算我去给人家送了东西,帮了人家,那也不关你的事儿啊是吧?你好像对我很不满,这个让我觉得很奇特,你知道吗?
夏佑至:她有解释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感觉吗?
范俭:不公平啊,对他们而言。他们当时所有的人都陷入到一种不公平的想象和不公平的定义里面。
社区是作为居委会这一级别的一个最基层的政府单位。如果说发放各种东西,给这个没给那个,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你要都不给就没事了,你要给了这个没给那个,那问题就一大堆了,问题就非常多。我们也同样被界定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大家把拿摄影机的人跟政府工作人员等同起来了。
有些居民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有一点积怨,在疫情期间就被放大了。第二家那位阿姨认为,应该把得新冠的这些人的所有信息,住在哪一栋、哪一层、几零几、名字……都公布出来,这是她的观点。社区实际上做到的是公布(新冠患者)在哪一栋,只把那一栋有一家还是有两家告诉给了全社区的人,但是具体哪家社区是不能讲的,也没有讲。所以在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些比较夸张的人的关系和言辞。但是那种最极端的或者说最苛刻的言辞,我并没有放到片子里。我觉得如果是现在,他们不一定是那样一种观点。
夏佑至:有意思的是,我们作为拍摄者会被动地介入到拍摄对象的关系里面去。如果没有拍摄,她可能就不会表达,或者说摄像机没有对着她,她可能不会表达得那么激烈。有两个场景我印象很深,一开始蔡大姐出去的时候,志愿者跟她说话,人家往前想要靠近他,她就不停地往后退。片子快结束的时候,正好他们又见面,志愿者说到“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自己要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把自己打开。”然后旁边其他居民过来,就来质问蔡大姐,什么样的人会得(新冠)?是不是唱歌跳舞的、业委会居委会这些人。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每个人突然都产生了一种要界定“谁是我们、谁不是我们”的冲动和紧张感。
今年看了很多报道和很多关于武汉疫情的片子。每个片子都有一种紧张感在里面,但其他片子中的紧张感,跟范俭这个片子里面的紧张感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等会要讲到的深来的片子《蓝盒子》,医院ICU里在疫情最后阶段的日常景象,那当然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紧张气氛。
范俭恰恰相反,他的拍摄对象也好,他拍摄的社区也好,生活都在逐渐走向正常。摄像机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时序从冬天转向春天、所有植物都开始发芽了、树开花了、鸟开始在上面叫了、生活也在逐渐地从一个“非常”的状态走向正常的状态。可是在生活走向正常的细节中,那种紧张感仍然挥之不去。在其他片子里,很少看到对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紧张感的展现,或者说他们只是偶尔涉及到,并没有把它很好地展现出来。这可能是范俭所有纪录片的特点——他总是从一个很日常的很小的细节(入手),不管是他关于四川地震的纪录片《活着》还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他展示的都是这样一种非常平庸平淡的日常生活细节,跟人内心巨大的情感波动之间,产生的强烈的对比。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范俭导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关于SARS的。SARS离今年17年了。正好深来也是在今年这样一个疫情里面,拍了他的第一部制片的作品。这中间可能有某种巧合的成分,但是我想它也并不纯然是巧合,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巨大的波动也确实会给我们的创作者一种召唤。
因为我跟深来平时互动得很多。还是在过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很想去武汉。但是等他介入到一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到了疫情的后期。他做的工作还挺多的,除了日常报道、做了他自己的片子,实际上他还担任了《被遗忘的春天》的制片人。我想请深来讲一讲到武汉后,这一系列工作,包括寻找拍摄对象,寻找拍摄地点,是如何进行的。包括怎么平衡你自己的拍摄和范俭的拍摄。
杨深来:主要还是跟范俭导演慢慢商量。一开医院,但范俭导演很希望能够去拍社区,所以才会促成《被遗忘的春天》这个以武汉社区为背景的故事。我在写故事梗概的时候,觉得社区可以拍出一些“日常中的非常态”的东西,医院里面,我希望能够拍到一些“非常态当中的日常”的东西吧。
具体的角色选取和地点选取参照了澎湃新闻的一些文字报道。澎湃之前报道过这个小区,文字记者写得很好,抓出了小区内部的一些矛盾。有了这篇文字报道,相当于是做了一点点前期的调研工作。3月中旬的时候,范俭也到了小区,又去做了一遍采访和调研,慢慢地摸索出了这样一些人物。
我们最早接触的一位大姐,很热情,提供了很多信息、介绍了一些人,然后又碰到那个在天台上种菜的大爷。这时候还没有定下来要拍谁。再往后,医院去拍片子,后期所有的这些事情主要就是范俭导演这边完成的。
在出发之前我其实问了好多人,医院到底合不合适拍?医院是在疫情下非常核心的一个空间,它能够连接起很多人物,很多角色,但是大部分医院是非常难拍的。我也担心过,医院拍摄。医院、寻找人物的过程,其实还是挺焦虑挺纠结的。很多医生的情绪曾经处在高峰上,但是慢慢地在拉锯过程当中变得很淡。医院、医院,医院。我们当时到了那边,感觉它的状态比较符合我出发前的预期。医院ICU主任胡明的个性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感觉很多东西可以继续往下发展。
但整个片子从拍摄到剪辑,也发生了很多预期之外的事情,很多东西需要我自己去反思和思考。
范俭:我补充一下,去之前我跟深来是有一个沟通,医院?我当时是医院。
首先我知道我更想拍社区。我在2月份的时候就希望有机会能拍武汉的社区,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去。我觉得社区在各个阶段都是可以拍出很多故事的,无论是最早期的混乱,到二月中旬的所谓大排查,以至于到中后期我们三月份要去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被关了一个半月甚至更久,在社区都是不停地有新的内容可以拍。
当你要拍武汉新冠肺炎的题材,医院是回避不掉的一个现场,是最容易想到的一个现场,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现场。我知道新闻现场是什么,但是我是拍纪录片的,是否一定要去所谓新闻现场或者第一现场?因为拍纪录片一定跟新闻报道的点不一样,或者说跟记者要选择的方向不一样才可以。然后我还要跟别的纪录片同行也尽量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大量纪录片同行也在(医院)。
基于我拍摄纪录片的经验,有一种蓝光效应。就是说当一个巨大的事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被最闪光的那部分,或者说最强烈的那部分吸引,那个就像黑暗里的一束光一样,直接照向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一下子被这束光给抓住了。但是如果说你只奔着这束光去,你可能会忽略整体。那个光其实只是庞大黑夜里的一部分而已。它如此强烈,会遮蔽了你要看的别的东西。这个经验我是有的。所以我会告诉自己,要回避蓝光,去看蓝光以外的日常生活。看经历疫情的普通人,最普通的人,而且真的还要离疫情稍微远一点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如何继续生活?那个我认为是蓝光以外的。
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选择,我就很果断地说我去拍社区,医院,深来你愿意拍,那你就去拍,但是我建议你要多加小心,要想好了再干,也要注意有一些防范吧。医院里拍摄,对于团队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是要做好各种准备。
夏佑至:到拍摄题材的选择,有一部分可能是一个创作者的个性使然,但确实有一些行业判断。我本来今天也想问范俭这个问题的,就是跟其他的纪录片导演相比,包括你们很熟悉的像周浩、陈为军这些导演相比,你的片子与所谓时代热点或者新闻事件的关系,我觉得跟其他导演还是有区别的。
从《反思非典》开始,然后四川地震后你拍了《活着》。当然,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多多少少总是以某种形式和年的地震发生了某种关联。不同的是,地震发生10年后,你还在持续跟进这件事,包括年你跟腾讯合作了《十年:吾儿勿忘》。年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主角余秀华也是非常热点的人物。我感觉你对热点是贴得很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选择跟其他导演的选择不一样,他们可能会选择距离热点更远一些。
范俭:我对新闻、对热点的东西和大事件是有敏感的。因为我本科是学新闻出身,有做过媒体的经验。但是如何去拍一个大事件,如何去切入热点的话题,我的切入点跟新闻的切入点是会很不一样。
夏佑至:你要去拍的这个社区,有三千八百多户人家,人口可能超过1万人。就算是澎湃的记者做了一些前期关系,有一些现成的关系可以找到,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把拍摄对象找出来、甄别出来,并且去跟进他,会有种赌一把的感觉吗?拍摄过程中会不会怀疑,我是不是跟对了拍摄对象?
范俭:我认为一个月足够我发挥了。因为我跟深来最开始商量的就是待一个月左右,我觉得一个月挺够,不是太短。因为我们最开始也不是想拍一个特别长的片子,而是计划拍摄一个30分钟左右的片子。再加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比较快地判断出来这个社区是有潜力的。
这个社区包括好几个小区,我们拍得最多的那个小区里有22个确诊病例,这在武汉所有的小区里面都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要拍一个有新冠确诊患者的家庭的话,我可以从22个里面去选,选择面还是比较大,即便我被20个家庭拒绝了。我相信我应该不会被拒绝这么多,不至于。这些还是要依赖摸排。
然后这个社区包含的空间是挺丰富的,除了那种典型的封闭式小区以外,它旁边还有一个像城中村一样的另外一个小区,彼此的空间特点和人群就不一样。城中村的那个小区更像是住了一些流动人口,那么封闭小区里的居民,根据我在很短时间里的观察,一多半是中等收入到中低收入的家庭,基本上是本地人。从口音、从交流方式、从他们家庭的摆设你都能看出来,他们在市民阶层里有相当大的一个代表性。
我们拍摄的那位社区干部其实是一个小惊喜。一开始文字记者了解到,这地方有个男性的书记非常能干,结果我们去的时候他病倒了,回家了。我们当时还小遗憾了一下,不能拍到这个风风火火的男性书记。然后我就问,那现在谁当书记啊?他们就说是一个女的副职,她才来当一线的书记时间不长,我后来就转念一想,女性也许更好,更适合我的拍摄。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
就像厨师,当你面对你拥有的这些材料,你要迅速地做出判断,这些材料可能能炒出什么菜来。我觉得其实去了两天左右,就大致能判断出来,它可以炒出最少30分钟的菜,但如果说我能找出更多的东西,那就是60分钟的菜,也是会有的。
夏佑至:你的几个拍摄对象里面,有一对生病的夫妻,女方是尿毒症,男方患有骨癌。有一个小插曲。今年寒假期间,有几个学新闻的同学找到我,说他们做了一篇疫情中的癌症病人的报道。因为武汉本身是中南地区的医疗中心,医院医院都在那里,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要去武汉看癌症。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原先在那边看病的很多病人,医院出不来,要么他就看不了病。比方说本来要做化疗,人在外面租房子,结果就做不了了。这种情况特别多,正好跟你片子面拍的一样。今天我特别通知那几个同学过来听一听范俭导演处理这类题材的经验,特别是那种情感上的克制。
在疫情这个特殊时间段里,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而且拍摄对象对拍摄的接纳程度也很高,他们也不断地在摄像机前面袒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整体上来讲,这条故事线展开的过程中,情绪是相当克制的。在拍摄这类情感很强烈的故事时,很容易有一种诱惑,就是经过导演和摄像机的选择,我们使它变得更加强烈。你在拍摄过程中如何处理这种情感的基调?
范俭:如果10年前我去拍这种情绪强烈的画面,我会希望它很强。对,我会希望它很强。因为这是一种戏剧性的时刻,这是一种人的情绪的宣泄,这个非常能够抓住观众,毫无疑问的。
但是现在,因为创作到一定年头之后,我不再觉得这部分多么吸引我。我反倒不是那么愿意去拍那种情绪很激烈的画面和场景。如果有情绪很激烈的,我反倒会站远一点,或者说反倒会收着点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多么有价值。我反倒会觉得日常性的、人的常态的情绪,或者说人的那种涌动但不宣泄的情绪,对我来说会更好。我喜欢这种情绪。
这要说多一点,如果是放在东西方的作品的比较里面,可能在西方的作品里面,会把那种情绪处理的特别强烈。但是在东方文化下,我会把情绪做得更隐藏一点,我希望情绪更绷着。情绪更绷着的话其实会更有张力。
杜进得了尿毒症,她还要照顾她得了癌症的老公。我们的着力点是拍这个女性。我们第一次拍完后,我对摄影师说,不是两个人都要拍得很细,不是他俩平均用力地拍。你着重拍的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承担的东西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后来我们的镜头是拍杜进多一些。而拍杜进的这些镜头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她站在窗户那儿背对着我们,在那抹眼泪。我觉得背对着就很好,而且我们不打算离近,跟她其实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就拍她的背影。我觉得这个背影非常动人。这个背影、窗口,她的肩膀似乎有一些动作,她手上有一些动作,但你看不到她的表情。我觉得不看表情是最好的,不需要看表情。你会感知到她的内心是什么,不是让你看到的,是让你感知到的。然后窗外有花在盛开,窗外的花当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一个角度,这些都是让观众在一种更丰富的情绪的现场里面去体验,而非直接的、单一的近景、一张脸、一个特写,那就太简单了。
刚才您提到在武汉得不到救治的癌症患者,其实数量非常庞大。武汉确实是一个治疗癌症的重要的地方。我早年前拍余秀华的时候,妈妈得了癌症,我就跟着医院,有过拍摄。那里面有大量的癌症患者。
在武汉期间,我遇见了一个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和他的团队,专门想要把武汉以外的癌症患者弄到武汉来去救治,因为当时他们进不来。三月的大概中下旬,这件事慢慢就有了一些可能性。周边的黄石或者孝感或者荆门的患者,他可以出来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进入武汉,进医院对接,医院有没有床位,等等。医院的癌症门诊是到三月中旬以后慢慢才开放的,之前没有门诊,原来住院的很多癌症患者也让他们出来了,不让住院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有大量的人想要进来。这批志愿者就干这个事。
当时我还挺想拍这个的,我还挺想专门拍志愿者把人给弄进来,要打通什么关系,然后这些弄进来的人身上有怎样的故事。病人都是一个家庭,他不是一个个体。确实在武汉期间有蛮多可以拍摄的题目。
夏佑至:在疫情这样的大事件里面,导演的诱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范俭刚才讲的,当我们站在读者、站在发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去寻找那种戏剧性的、情感更强烈的那种时刻,我们好像总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在主动寻找这样一个时刻,有些导演甚至会忍不住去push这个时刻出现。特别是对一个年轻的导演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不知道深来置身在ICU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诱惑?另外,你这部片子的素材量特别大,据说有2万分钟素材,为什么拍了这么多?
杨深来:医院拍摄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有“赌”的成分。拍摄的时候,有时候心里还会想就是赌一下,这里如果没有出来什么特别好的故事,可能就属于赌输了嘛。
但实际上进到ICU去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是比较清楚的,我也不想依靠那种特别紧张的、特别生死离别的东西去支撑这个片子。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所以拍摄的时候就一直想找到一些不同于常规的细节或者情感。说实话,我觉得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始终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并不会把ICU里的生离死别作为故事的卖点。
在ICU里拍摄的时候,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去做出一些预判,所以停机的时候比较少,很多时候都是一直连续地在拍。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带着预设进入的,但这些预设完不成、达不到,很多事情发生得和你的想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用了无差别拍摄的方法,看到什么东西就先拍下来,所以素材积累了很多。我希望前期能够拍尽量多的内容,然后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再去挑选,所以素材料特别大。
夏佑至:这个可能是我们学习过程中交的学费,很难避免的一个过程。《被遗忘的春天》里线索很多,虽然每条线索的比重不同,比如说在阳台上种菜的那个人物,可能起到的表意的作用。但要拍摄这么多线索还是相当不容易。范俭的拍摄团队不大,制作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你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对年轻导演、对我们学习新闻和纪录片的同学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经验。
范俭:对,这是一个需要经验,需要现场的判断的。总的来说这次我是去之前就决定要拍群像,这个想法是已经确定,我不是要拍单独的一家人或者单独的某一个人,因为我要拍的是社群关系,我在出发之前就决定把社群关系这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来拍,那我一定要有一个群落。
我过往的几部作品都不是群像,《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其实《活着》也不算群像,虽然他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家庭,但我们最终呈现出来是一个家庭。那么我为什么以前不太拍群像呢?就是因为这个坑很多,拍群像不好拍。
最大的坑有两个,第一个坑就是每个人你都会拍得语焉不详。第二个坑就是,你的后期的结构怎么建立?你的人物关系如何去建立?它们如何去交织在一起?你建立的人物越多,越难剪辑,越难交织。
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不会选择群像拍摄,但这次需要这么做,那我就在头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做加法,甚至在头10天都是在做加法。我在小区里到处套瓷,认识各种各样的人,首先我确定肯定要拍一个有新冠患者的家庭,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我一定要去拍到的。
第二,我要找到两极中的另一极,也就是对患者有反感的人。在这两类之外,我也在社区里看到了很多的中间人群。第一种特别吸引人注意的中间人群,就是志愿者。他们在政府和社区提供的服务以外,自己去团菜、团牛奶之类的东西,为社区的其他人提供服务,我在武汉后来了解到的很多社区都有这样的人,就是热心人、志愿者。我觉得这是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的另外一种典型人格。其实我要拍的是一个社区里面的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人格建立了不同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热心的、乐于助人的、善意的这样的一个人格,肯定是要拍进来的。蔡大姐就到走廊去领牛奶,有个女孩说你不要刻意跟我们拉开这么大距离,那个女孩就是个志愿者,她虽然也愿意被我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能进入到她的家庭里面,她的家里面有小孩,有老人,然后她的老人比较介意我们进进出出,万一影响了小孩怎么办。所以我只能拍到她在社区里,每天或者每隔一两天在那组织大家搬菜,拿牛奶之类的事情,我不可能深入到她的家庭内部,她的老公我也拍不到,她的小孩我也拍不到。后来虽然我们也拍了很多她的这一类的活动,但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并不觉得她能够成为一个主角,是因为她的层面太单一了。
还有一个早期决定一定要拍的,就是在楼顶种菜的刘叔,去武汉之前就见过文字的报道里写到了他,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我一定要去拍的,为什么?因为首先是很有画面感,在楼顶种菜本身就是很有画面感,他的动作也很多,画面也很多。第二是他的心态,他那种淡定的心态在当时是不多的,这种淡定的心态是怎么建立的?就因为他用种菜、养鸽子,这样一种行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生活秩序和生活哲学。这套生活秩序和生活哲学并没有因为疫情被打断,他以往也是这样的,他往年也是在春分的时候要干嘛,谷雨的时候要干嘛,今年还是如此,唯一受影响的只是他的鸽子不能够飞出去了。在一个社区里面或者在一个灾难里面,这种人会很特别。以前我拍过汶川地震,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说在地震以后很快为自己建立一套秩序,生活秩序,而且非常规律。这样的人就会很快从这种灾难造成的焦虑或者心理破坏中走出来。种菜的大叔这样的人格是应该去被展示出来的。
这就是我在小区里前一个礼拜必须得要找到和拍摄的,并且这几种人我都在拍。关系的建立要更难办一点。我再补充一点,生病的那对夫妻,杜进和黄冲,原来不在我的预期之内来拍的,只是跟着社区干部(陈琦),我整天偷听她的电话,她电话很多,她有很多一部分电话是跟这些病患沟通,跟癌症患者家庭或者说尿毒症患者的家庭,所以我就听到了他家是这么一种情况,女的得了尿毒症,男的又是癌症,然后我觉得这种处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困境。而且我当时到小区第一天就注意到,这个小区里至少有四五个需要透析的人,每隔一两天都要去透析。我想看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困境。
但是当我拍到4个到5个角色之后,提醒自己不能再多拍了,再多拍一定会进坑,一定会很麻烦。所以我后来还认识了一些新的有趣的人物,我都没有再去拍。即便如此,到了后期剪辑的时候,剪辑师说拍的还是太多了,线索还是太多了。
对剪辑师来说,他要做的第一是减法,减谁?把谁来突出?主线人物如何去突出它,不是主线人物的如何去做减法。比方说种菜的刘叔,我们拍了很多他在家庭内部的生活,他跟他爱人每天都在看新闻联播,每天去看武汉的数字,去看各种外界的信息,然后他们评判小区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我拍了不少,但是后期剪辑师决定这些都不要剪进去,因为她判断,真正能抓住观众的是另外两个家庭。
一个是蔡大姐家,得了新冠的家庭,这个家庭本来就有三个人物了;另外一个就是杜进的家庭。这两个家庭你必须要作为主线,不能被其他的太多的枝蔓影响。先搭主干,剪完了主干之后,再剪那些枝叶。剪辑剪主干的时候,其实只剪了三组人物,蔡大姐一家、杜进一家,再由社区干部陈琦来串起来这两个家庭。
陈琦实际上是一个串场的人。在前10来分钟她是一个串场的角色,而刘叔等人我都是后面剪完第一稿之后再加进去的。我们是先剪了树干,然后再加的那些细枝末叶,先保证你的主干是强壮的,是完整的,你的主干的线索的基本的构架先有了,再加一些别的。包括一些志愿者都是后面第二第三遍剪辑的时候加的。包括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空间的镜头,比方说那些花、那些植物、狗的镜头,那都是在第三第四遍剪的时候给加进去的,是这么一种方式来完成选择的过程。
夏佑至:刚才说到导演会面临两种诱惑。第一个就是对戏剧性的追求。第二可能就是范俭刚才说的,当你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会发现很多可拍的东西,不停认识有新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物有自己的故事来刺激你,使得你就会不停的陷入这样一种选择。我要不要拍这个人,我要不要跟进他?刚才你说的那个帮助癌症患者到武汉去进行治疗的志愿者团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对一个导演来说,这种诱惑在拍摄过程当中是始终都存在的。特别是当这个片子是群像的时候,更是如此。
一开始就想问你关于在楼顶上种菜的刘叔这个人物,从你给他在叙事里分配的功能来说,我猜想你可能拍了更多关于他的画面。所以一旦你拍到了那么多的画面,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导演和剪辑之间的冲突就更容易发生。在剪片子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时刻吗?两个人必须坐下来讨论怎么来解决对片子不同设想的冲突。
范俭:这是经常发生。有时候导演有两个很大的缺点。首先是自恋。很多导演会比较自恋,觉得我拍的都很牛逼的,你都应该剪进去,或者我拍得都挺好的,你怎么就不用进去?这是自恋。
其次,导演会由于自恋导致很不客观。面对着素材的时候,他离自己的内心更近一些,但他离观众就比较远。而剪辑师就会要离观众近一点。以前我们最开始接触剪辑师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有一个词,叫keeponobjectivity,保持客观,剪辑师干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持客观。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对于导演的这种主观来说,这是需要的。
纪录片的那种故事性也罢,结构性也罢,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是到剪辑的过程中才成立。它不是成立于拍摄过程中。所以讲故事讲得好的人,其实更多的是剪辑师,不见得是导演。纪录片的故事要在剪辑的过程当中讲出来。作为导演要找到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又适合讲这种故事的人,同时你要告诉自己,导演不见得是最好的讲故事的那个人,然后你就要去信任剪辑师。如果说缺乏信任的话就很难办,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家最终费了半天劲,剪出来东西被导演给彻底给否定了,这事也挺不好的。
当然我的工作里倒不存在这种情况。我早年间合作的剪辑是马修,是法国著名剪辑师,我跟他合作了《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等等。基本上他在电影剪辑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厚了,所以绝大多数时候我是相信他的判断,所以我跟他的争论会很少。那么但这次剪辑师是我太太臧妮,应该说她并不是一个像马修这样的老道的剪辑师,但是臧妮毕竟也拍片拍了很多年,我们一起拍了很多年。而且她是女性,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来看我拍的素材,特别是当她看到《被遗忘的春天》里的这些角色,她有她的很多的触动。
我拍完一个礼拜,就把素材压缩,通过网络传给她,她就开始看了。她看了之后,我们还在武汉的时候,她就会反馈一些意见,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剪辑师看了一些素材,会形成一些很好的视角,告诉我还缺什么,或者说这个镜头的表意还怎么不够,那么我们再去补拍某一个镜头,比方说我们之前拍鸽子,刘叔的鸽子,我们实际上还是比较写实的拍法。然后剪辑师看到素材之后说,你们能拍得更表意一点,就是你们要钻到笼子里拍鸽子,拍摄鸽子被笼子困住的这样的一种表意的镜头。OK,我们就这么来操作了。我觉得这种与剪辑师的合作方式非常重要。
在具体的剪辑当中,其实我俩吵架吵得很多,但是应该说只要她能够说服我,用她的合适的理由来说服我,都会说,好,你是有道理的,那我尊重你的这个道理,就按你说的来办。十次争吵里面,七八次我还是被说服的。我愿意去倾听,还是要倾听剪辑师的意见。比方说对于刘叔这个角色的做减法,我觉得她的这个理由是充分的,因为她觉得,第一,刘叔家庭内部的张力没有那么大。第二,刘叔这家人跟其他人物不怎么来往,没法建立很有机的一个关联,对于剪辑来说,很难捏到一块。只能把他做成符号化的角色。基于这样几点理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所以就按照她的意图就做了大量的减法,这样的情况还是蛮多的。
以上为分享会实录的上半部分
海报设计:冯子凡
文字整理:艾克达、朱佳程
插图由嘉宾提供并惠允使用
原标题:《分享会|拍一部纪录片有多少坑》
转载请注明:http://www.kohkf.com/wazlyy/13519.html